

11
那晚,我在他的房間裡吞雲吐霧。
抽完了,我懶得找煙灰缸,隨手摁滅在他昂貴奢華的床單上。
我一點也不像他眼中嚴肅正經的中學老師,反而像那些娼婦、那些妓女。
「你為什麼要裝成這樣?」他又好笑又無奈地靠在窗邊打量我,「就為了讓我覺得,你沒那麼像她,然後我就會放了你?」
我閉著眼,又點燃一根:「那如果,我本來就這樣,是你錯看了我呢。」
唐清川笑著撇過頭去,摸出火機正要點上手裡的煙,被我猛然喝停:「不許抽,說好的,戒了。」
他像犯了錯的孩子,兩手無處安放,半晌小聲申辯一句:「你怎麼只許州官放火,不許百姓點燈!」
「誰叫在這兒,我是州官,你是百姓呢?」我歪著脖子答他。
「好好好,白老師,您是我姨太太,就該您說了算。」
好在,我的反常沒有太久。
第二日我早早起了床,得體地裝扮好,得體地吩咐下人做事,得體地去檢查唐鬱的功課。
我不斷試圖去逃避一個問題,我昨晚到底為什麼會那樣,是因為唐清川的粗暴和 厭棄嗎,還是因為我阿娘口中不知所云的大少爺。
我不知道。
唐清川洗漱完下樓,看到我慣穿的白色旗袍和素雅寡淡的臉蛋,眼中閃過一陣驚喜,緊跟著又是一陣失落。
驚喜于還好我不是真的娼婦,還像他那讀過書,擺得了高姿態的嫂嫂蔡綿綿。
卻又失落于我已經正經而無趣,給不了他歡愉。
「週五晚上有個舞會,你和我去。」餐桌上,他低著頭吩咐。
我一向不忤逆他,點點頭道:「好。」
「久霜,你也知道最近外面的形勢,風雲變幻,莫測得很。」
他突然話鋒一轉,說了些不明所以的話,
「也許,不知什麼時候就開戰了。我是一方軍閥,平日你說我作威作福也好,說我隻手遮天也罷。可到最後,國家必然是要統一的,我們鬥來鬥去,最後槍桿子也要對外,去保家衛國,去血戰沙場,去趕走洋鬼子。我最近在想,鬱兒也都那麼大了……」
唐清川難得地絮絮叨叨,說起話來還莫名地顛三倒四。
我費解地擰起眉:「司令到底想說什麼?」
「所以,我想……」面前這拔山舉鼎的漢子居然低垂著眉眼,臉紅了起來,「咱們要不,也趁著這安生日子,要個孩子?」
我一口熱豆漿嗆得咳嗽連連。
「我知道這事兒不能急,久霜,我也不是在逼你。」
他小心翼翼地拍拍我的背,一邊急吼吼地眨巴著眼分辨,「昨兒我聽那什麼大少爺,我心裡難受得緊,我是生氣了,也實在是怕呀……」
「怕什麼,你是司令,你能怕什麼?」
「怕我哪日戰死,你就真同不知哪家的大少爺跑了!」
他氣鼓鼓地紅著雙頰,想要拍桌子,手落下後卻是輕輕捧住碗,「所以久霜,我也老大不小了,是時候該給人當爹。」
「這事兒往後再議吧。」我收了自己的碗筷,站起身,「司令得快些去指揮部,這都幾點了。
」
12
到了週五,舞會的日子。
蔡綿綿掏出了一套自己珍藏的翡翠珠寶,親手把項鍊戴上我頸脖,對著鏡子左看右看:「漂亮吧,清和送我的。」
她陶醉地盯著正中最閃的那一枚,「從前他帶我去舞會,最喜歡我戴這一套。可惜了,自他死後我就再沒機會戴了。」
她眉眼間逸出一絲感傷,嘴上硬硬道:「你也別誤會,我不是對你示好,只不過不想你這副窮酸樣,丟了唐家的顏面。」
我不說話,順從地讓她打扮著我。
哪怕在我心裡,她拿槍指我的事兒沒完,什麼充好賣乖都消不了。
直到她滿意地拍著手,要拉我出去讓唐清川看看的時候,我驀地開口:「這套珠寶,有什麼淵源嗎?」
蔡綿綿被我問蒙了,打量我一圈,像是被戳到了痛處似的,羞惱地恢復了跋扈:「你是什麼東西,也配打聽我的事兒?」
然後她奪門而出,留下唐清川不明所以,看看我又看看她,最後還是慣性嬉皮笑臉地追在她後面哄。
也不知哄沒哄好,去舞會的路上,唐清川半是好奇半是嗔怪問我:「方才是怎麼又惹了她?」
「我惹她?我哪敢惹她,怎麼就不能是她惹我?」我不知哪來的脾氣,突然沖陳副官喊道,「停車,我不想去這舞會了。」
陳副官愣了下,開得慢了些,一邊笑著回過頭問我:「怎麼了白小姐,是有什麼東西落府上了嗎,回頭我給您取去。
」
「別理她,你同她說什麼廢話。你看看她現在,這股子任性勁兒,像不像大太太?」
唐清川指著我,故意激我,「白久霜啊白久霜,你才是真為了討好我無所不用其極。怎麼,你這樣耍性子,這樣鬧脾氣,你就更像她了?你更像她,我就更寵你了?」
什麼混帳話,卻說得我真無力反駁。
見我沉默地鼓著嘴,他更起勁:
「你要學也學點好啊,她是大戶小姐,最是端莊,最懂禮儀,你怎麼不學?你知道嗎,她從前也不是這副模樣,可惜三分自作孽,七分命不好,最後生生被逼成這樣。」
「你既然這麼心疼她,倒不如枉顧世俗娶了她,可不比你四處尋這些半吊子的替身強過百倍。」
「你懂什麼?她恨我都來不及,殺了我都不解仇,怎麼會願意嫁我。」
說著,唐清川一把勾著我脖子把我鎖進懷裡,咧開嘴笑得沒個正經,
「哪裡有你好,又知書達理,又乖巧聽話。今晚,就今晚,咱們回去生個大胖小子,以後讀書比鬱兒好,氣死那小寡婦!」
聽見前排陳副官的笑聲,唐清川嘖著嘴啐道:「笑什麼呢,開快點,老子迫不及待要讓那群人看看我金屋藏嬌的寶貝了!」
13
舞會上,唐清川熟稔地領著我與一眾權貴談笑風生。
「沒想到啊,白小姐是位教書育人的女先生,難怪氣度不凡。」
那些人恭維著我,也就是恭維著唐清川,誇得他哈哈大笑,對敬過來的酒來者不拒。
我免不了也喝了些,唐清川說我喝酒的姿勢有趣,閉著唇把酒汁兒送進去時,不像象牙塔里的女老師,倒是活像位貴族小姐,比蔡綿綿還蔡綿綿。
「你到底看不看得准人?」他要碰我手中的杯子,被我拿開,「也許,我是個千人騎萬人罵的娼婦,也不一定呢。」
「娼婦?你要是娼婦,就這死魚似的表現,怕早沒生意餓死了吧?」他在我耳邊嘲我,趁我生氣前一把將我攬懷裡,拉去和下一位軍官推杯換盞。
酒過三巡,我喝得有些不適,唐清川送我去車上休息。
我渾身熱得慌,一隻手拉著他,一隻手就開始解旗袍扣子,嚇得陳副官趕快紅著臉扭過頭。
「你幹什麼呢,想脫衣服等回到老子床上,你愛怎麼脫怎麼脫,到時候你再脫個夠!」
唐清川說著脫下外套蓋我身上,被我一把掀開,他又要給我系扣子,我又掀他手。
如此三個來回,他惱了,按著我的雙手就壓上來:「有完沒完,你這樣子哪裡像個老師?你真他娘的像妓女!」
「我就是啊,我就是。」我拉著他的袖子,湊在他耳邊,曖昧地呵著氣,「唐公子,你別走,你給我三個大洋,我保你今晚高興。」
陳副官聞言尷尬地剛想跑開,就被唐清川一口叫住:「身上帶錢嗎?」
「帶……帶著呢。」
「聽不見嗎,她要三個大洋!」
唐清川惱了,他直接拉過來陳副官,從他褲子口袋裡摸出一把,盡數塞我手裡,「來,白久霜,你要的錢,老子今天倒要看看,你怎麼讓老子高興?」
我一把將他按上後座,食指繞著他下頜。
唐清川竟是害羞了,我剛要撕扯他的襯衣,車窗卻突然被扣響。
我惱火地循聲望去,那是一張年輕女子的臉。
「扶桑?」她喜出望外地叫我,「你是扶桑嗎?」
「不是!」迷蒙著眼,我不耐煩地答,「你認錯了,這世上同我相似的女人太多了。你見過唐府的大太太,蔡綿綿嗎?她呀,和我樣貌也十分相像,興許,她才是你要找的人。」
說罷,我懶得同她糾纏,又迫不及待搖上車窗。
14
我和唐清川抱著親著,一路從門外擁吻著進來,再上樓,再入室,當著蔡綿綿的面,怎麼也不肯鬆開。
「惡不噁心!」她站起來把報紙摔得滿地都是。
我推開唐清川的腦袋,回頭沖她喊了聲:「不愛看別看!」
那一晚,我終于不像是死魚。
我纏著他,攪著他,叫他屢屢沖上雲霄,到繳械投降。
我承認,我盡興了。
哪怕是因為,我把他當作了另一個人。
不知是幸與不幸,翌日一早,我竟是將昨晚發生的一切忘得乾乾淨淨。
我印象中的最後一幕,還是在舞會上和某位青年才俊互相吹捧,然後飲下手中的酒。
之後發生的種種,都只在唐清川的口中。
他說我是怎樣怎樣浪蕩,怎樣怎樣瘋,還叫我不信去問陳副官,問蔡綿綿。
唯獨扶桑兩個字,他絕口不提。
我不理他,任他如何說,只埋頭喝著碗裡的粥。
直到他難得的正色:「久霜,昨晚那麼多軍閥權貴聚在一處,你應該明白,這不只是一場紙醉金迷的舞會。
」
他深深地吸了口氣,「外面,可能快要變天了,我得為你,為唐家安排一條後路。」
「我的命輕賤,若真生了變故,我便回學校去,任憑流彈射穿我腦袋。」酒醒之後,我總是不冷不熱。
「別說這種話。」他嗔怪地把我摟進懷裡,「你是我唐清川的人,我不許,出任何事兒都不許。」
15
那之後,唐清川的公務明顯相較之前更是忙碌。
可就是這微乎其微的空餘,他還不忘辛勤耕種。
甚至,他特意請來醫生,搓著手局促地請教:「您看我唐某人,是不是有什麼不好說的毛病呀?怎麼我這正值壯年,太太卻遲遲懷不上呢?」
太太是明媒正娶的妻子的稱謂,按理說,我配不上他這樣叫。
那醫生看看他又看看我,說要取我倆一管血回去化驗。
唐清川立刻護犢子地擋在我面前:
「這不好吧,我平日裡看她嘴唇破個皮心都顫得疼,您這上來就要一管血?要不您看,多抽我三管,抵她那一管,行不行?」
那醫生說了一堆解釋,還摻著些洋文,直到最後氣得要甩袖子離開,唐清川才終于首肯。
三日後,醫生又登門,二人在緊閉的書房裡討論了半天,唐清川終于陰著一張臉出來。
送走醫生,他迫不及待沖到我面前,攢著我胳膊,力道大得想要把它擰斷一般,把我從唐鬱身旁一路擰到他的房間,狠狠甩在地上。
「拿出來!」他大著嗓沖我吼。
我從未見過他如此慍惱的模樣,不住往後蜷縮著:「什麼?」
「我叫你拿出來!」
我不說話,只怯怯地盯著他。
「別裝了白久霜,別裝可憐,也別裝蔡綿綿!是,老子是識人不准,錯看了你!老子以為你他娘的就算是團冰,有一天也能化吧!何況你不過是個身世清白簡單的老師,以為你能耍出什麼麼蛾子!」
他說著不解氣,又揪著我的領口將我提起來:
「可為什麼啊白久霜,到底為什麼,就為了當初我縱她開了那一槍,你就要這樣對我?好,就算你恨我,可那之後,我對你不夠好嗎?你明明知道,我就是想要個孩子……」
說到孩子,我就明白了他的火光。
我推開唐清川的手,踉踉蹌蹌地站正:「你想要,又不代表我也想。」
我知道這話他聽了要震怒,可我偏偏要說。
果不其然,唐清川反手從抽屜裡掏出一把槍,抵上我額頭,並上了膛:「你信不信老子崩了你?」
「唐清川,是你逼我跟你的,又不是我願意的,你憑什麼覺得我就要心甘情願給你生孩子?」
我毫不畏懼地看著他,「你是什麼好人嗎?你的手做過什麼,你自己最明白了。你想崩我就開槍,反正,我也不是第一次被你們叔嫂倆用搶指著了。」
後半句話一出,他倏然氣焰不再。
他垂下手,指著我問:「行,我不崩你。你告訴我,你把避孕的藥藏哪兒了?」
我報了個地方,唐清川氣急敗壞地吩咐下人去找。
剛踏出去,他半隻腳又踩了回來,沉聲對我道:
「你若真厭我憎我,過不了多久,便也不用再忍我。人說一日夫妻百日恩,倘若你對我不算全然無情,那待到什麼時候我馬革裹屍,泉下泥銷骨,你多少念著點我的好。老子被你絕了後,只能等你給我燒紙!」
16
我本以為,經過此事,他會冷落我,或作踐我。
但事實是,都沒有。
他是惱了,是雷霆大怒了,卻又在爆發之後當作一切不存在那般。
我們還是同寢同食,他與我玩笑,也與我歡好,然後一如既往說我是條死魚。
我來了月事,他就不碰我,紅豆紅棗一碗一碗地熬著。
一邊盯我喝下去,一邊不斷地絮叨:「那天可心疼死老子了,以後再也不信洋醫生,那麼一管子血啊,你這小細胳膊,他怎麼下得去手。」
「別忘了,我只是你嫂嫂的替身,犯不著你心疼。」我有意懟他。
「老子愛心疼就心疼!」
而事實上,我是蔡綿綿替身這件事,唐清川一天也沒忘。
他會在休息日的清晨迷迷糊糊地側過身抱我,頭埋在我頸窩又親又蹭,可半晌叫出的卻是:「綿綿。」
他碎碎叨叨地念著:「綿綿,對不起,但我沒辦法,真沒辦法,我得殺他。」
我轉過去一把推開他。
唐清川悠悠醒來,不由分說又將我鎖進懷裡:「別動,難得今日休息,再陪老子睡會兒。」
可惜了,擾他美夢的不只是我。
他憩過去不到十分鐘,電話響起來,唐清川罵著娘地走過去接,不出五秒就清醒過來,披上外套,盯著一頭蓬鬆的亂髮就往屋外走。
「怎麼了清川,今兒不休息日嗎?」到了樓下,客廳中陪唐郁玩的蔡綿綿攔住他。
「出了點事兒,去趟指揮部。你聽我說,最近時局不穩,外面亂得很。」他叮囑道,「我不在的時候,門窗都關好,別出去亂跑。我會增些守衛,你保護好自己和鬱兒。」
說完,他回過頭,對視上杵在樓梯上衣衫不整的我:「我屋裡有把槍,你知道在哪。誰敢欺負你,」他做了個上膛的手勢,「你崩了他。」
說什麼大話呢?
要是蔡綿綿欺負我,還不知是誰崩了誰。
17
唐清川那一趟去了很久。
蔡綿綿嘴上不說,擺足了副無所謂的樣子。
只是平日裡,她不到九點便早早睡去,而那一夜,她在客廳守到淩晨。
最後打著呵欠熬不住了,還不斷往屋外看去。
我睡到半夜醒來,看見客廳還亮著燈,給她拿了條毯子去。
蔡綿綿卻並不領情,扭過頭啐道:「外面討回來的姨太太就是沒有德行也沒有心,丈夫還沒回來呢,自己先睡成這副模樣。」
我沒理她,徑直坐到她對面坐下,摸出煙扔到她面前:「抽一根,提神。」
「我不會。」她突然又像被觸到雷區,冷笑著罵人,「我又不像你們這種下九流的女人。」
「我們?」我點上火,雙指夾著煙尾輕輕晃動,拿捏著她的失態,「我們是誰?」
她不說話。
我等煙燃盡,便先回了房。
五天后,唐清川回來了,他話都沒和我說一句,直直沖進蔡綿綿的房。
房門一鎖,他待了整整三個小時。
唐清川這人是有點意思的,他喜歡蔡綿綿,誰都知道;他調戲蔡綿綿,誰也都看在眼裡。
但他就是連蔡綿綿一根手指都不會碰,甚至獨處的機會都不給自己留。
如今三個小時的孤男寡女,足夠人浮想聯翩了。
更有想象空間的是,門打開,蔡綿綿披頭散髮,滿面淚痕。
我不問,唐清川也不說,他看看表,匆忙把我拉到一邊,然後捏捏我的臉,擠著一切時間要調情:
「小東西,你又瘦了,是不是我不在你都不喝紅棗粥了?」
「還要走?」我躲閃著。
「嗯,下一趟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。」他不無擔憂地往樓上看了一眼,「你幫我照顧好她,這些日子裡就讓讓她吧。」
「她若拿槍指我呢,要讓嗎?」
「不會了,她不會了。」唐清川長長歎了口氣,「不是她的問題,也不是你的問題,是這世道出了錯。但總有一天,都會好的。」
18
蔡綿綿白天哭晚上也哭。
最後還是唐鬱告訴我,這一切,是因為他外公死了。
叱吒商場的蔡老闆,拒絕和洋人合作搞軍械生意,前不久在商船上被殺害,蔡家滿門老小,屠戮得不剩幾人。
原來這世間的人都一樣,苦難加身。
後來那些日子都是我領著唐鬱,帶他吃飯睡覺,帶他嬉戲讀書。
直到有一天,蔡綿綿終于肯下樓,她白衣素裹,不施粉黛,瞧著我倆更為相像。
「今天辛苦你了。」那是她第一次稱呼我,「白老師。」
人的心氣被抽幹就是一瞬的事兒。
蔡綿綿的命仿佛比這世上的人都已好上太多,卻還是逃不過夫君早逝,如今又家破人亡。
她被磨得沒了一絲鋒芒。
她憔悴地走到桌邊,拿起那天我扔下的煙,左右看著,驀地張嘴道:
「我認識你,白老師,一早認識你。那日,清川把你領回來,讓你給鬱兒講學。見你的第一眼,我就什麼都明白了。」
我不自主地顫了一下,就像見她的第一眼,我也悉數明瞭了一樣。
「說句真心話,我恨你一場,你不冤枉吧。我就是那一槍真射穿了你的頭,也是我該報的恨。」
她望向我,只是此時,眼中已泯消了恩仇,「對嗎?你就是,沈扶桑吧?」
我無言以對了。
關于沈扶桑的那段過往,到底還是要被她揭開。
「這世上,可能沒人比我更了解你,我把你當學術一樣研究,當事業一樣用心。你知道,我讀了多少信,讀了多少他寫給你的信嗎?」
她抽出一支煙叼進嘴裡,挪來挪去,卻怎麼也不像個樣子。
「我什麼都知道,知道你是怎麼從一個承歡男人身下的下九流,到邂逅了唐清和。又是怎麼被他一手調教成後來的模樣,國文、唱曲、打槍、【房☆事】,無一不通。」
「我知道他給你改名,他說扶桑木同根偶生,相互扶持生長,而如今這亂世,誰和誰都難兩廂攙扶。
所以,後來他也順理成章尊崇父母之命,遠渡重洋,與你離散。我都知道,全部,我都知道……」
我突然感覺自己赤裸了,渾身的衣服被撕碎,就這樣一絲不掛地站在她面前。
原來,我一直以為的隱藏,在蔡綿綿面前是如此昭然若揭。
是,她說的沒錯,我是沈扶桑,一個爛泥一樣墮落的女人,卻被唐清和捧上了天堂。
「為什麼不揭穿我?」
「有必要嗎?揭穿你做什麼,讓清川看看,我也就是個替身,是他哥眼中一文不值的女人?」
蔡綿綿抬起頭,她不倫不類地叼著煙,故意裝出熟稔懶散,開口卻是三分孤傲,七分乞求,「沈小姐,你瞧,我這樣看上去,和你像嗎?」
一時間,我不知該說些什麼。
她又繼續問我:「我覺得我和他信件裡寫的那些你已經別無二致了,可為什麼,直到死,清和也沒好好瞧過我?」
19
蔡綿綿口中,她一生最恨兩個人。
其一是沈扶桑,一個命原比蒲草還賤的女人,為了活命承歡他人身下,卻占了她丈夫的心。
其二便是她爹,她爹蔡老闆無視她與唐清川的感情,只為長子可以襲承軍閥之位,逼迫她嫁給唐清和,做心上人的嫂嫂。
「那會兒,多少名門望族,上趕著要嫁給清和。可他只看了一眼那些照片畫像,便選了我。」蔡綿綿苦笑著問我,「你說,這是為何,沈小姐?」
我哽住了,說了什麼都是在彼此傷害。
她羨我,我何嘗不羨她,縱然短暫,但到底,她才是唐清和的妻子。
「從小到大,我都沒有違逆過父親。嫁給清和之後,我隨他去了日本,逼自己忘記清川,對他完完全全敞開心扉。可無論怎麼百般討好,他也只有醉酒後才會看看我的臉。那一晚,他嘴裡不斷叫著扶桑,才和我有了鬱兒……」
蔡綿綿的淚珠兒一串串地往下滾,人原是有這麼多眼淚的,怎麼流都流不完。
「我能做什麼呢?除了截下他寄回來的,收件人是沈扶桑的信,學著他描述的扶桑,一點一點地模仿,沈小姐,你告訴我,我還能做什麼?」
她突然抬起頭,彎起微微搐著的嘴角,「所以,我恨你,想拿槍崩了你,我真的錯了嗎,真的十惡不赦嗎?你嘗過那種滋味沒有,被當作一個替身……」
很不巧,我點點頭:「我嘗過,真的嘗過。」
都是因果,是輪回。
冤冤相報,誰也逃不了。
「媽媽別哭了,鬱兒陪你玩吧……」被奶媽抱著的唐鬱還是跑了過來,把腦袋枕在蔡綿綿的膝蓋上。
「好。」她親切地沖唐鬱笑著,和詰難我時判若兩人。
牽走他之前,蔡綿綿抬頭和我說:
「白老師,我知道你為什麼來這兒,也知道你想做什麼。你若成了,那是遂你的心願;你若沒成,那也是你的造化。」
「我什麼都不會說,你的身份,你的目的,你的過往,我權當不知道。我只提醒你一點,曾經,我想和你做一樣的事情。
但後來我才知道,很多事兒,不只是我們看到的那樣。」
她站起來,走出兩步又回過頭,添了一句:
「我知道,你很想要那些信,那些年清和從日本寄回來,卻被我截下的信。但就當我自私,當我捨不得,總之,我不會還給你。這是我,最後的報復了。」
她自嘲地笑著:「很無力,對吧。」
20
唐清川再回來的時候,我和蔡綿綿在同一張餐桌上其樂融融地互敬著酒。
不想她酒量比我要好,我已然癱倒時,她還清醒無比。
唐清川看得差點驚掉了下巴。
彼時,他灰頭土臉,像是從戰場上爬回來一樣。
聽見蔡綿綿這樣說他,唐清川大咧咧地捋起袖子,一大塊焦灼的新傷:「對啊,老子就是戰場上爬回來的,哪像你倆有這好福氣,還能花老子的錢喝酒作樂。」
他插著腰啐道,「呸,那曹督軍真是好野的心,和洋人謀劃要吞併了我,還要給他們出讓土地,真他娘的畜生,賣國賊。」
蔡綿綿聞言嚇得嘴都合不上,又是關窗戶又是壓低嗓:「你這傷還好嗎?」
「一枚子彈穿過去了,沒事,你看,還能動呢。」他揮著胳膊,哪怕疼得齜牙咧嘴。
哄走他這位嫂嫂,唐清川迫不及待地抱著我又親又啃。
我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推搡著他:「別鬧,你在流血呢……」
「就是豁出去這條命,我也要死你床上啊!」唐清川才不管,連拖帶拉將我往房裡搡,一邊罵罵咧咧,「幾個菜啊,又給你喝成這樣。
」
他費勁地把我摁上床,我就勾著他脖子往他懷裡爬:「別走了,別走,別丟下我。」
「行。」他苦笑著,「真不知是福氣還是冤孽,一會是死魚,一會是妖精。」
那天完事兒後,他就這樣抱著神志不清的我,困乏地合上眼,嘴裡一會是咒駡,一會是哀思。
他從慈禧太后開始說,說到如今的世道,說到洋鬼子,說到其他那些割據的軍閥。
他和我說:「你信嗎,久霜。無論現在這天下是什麼樣,但總有一日,終歸是一軌同風,是海晏河清。」
見我不答話,他又環著我的身子,拉著我一雙手,輕聲問我:「我若有一日不是司令了,進退維穀,自己都難以保全,你想我如何安置你?」
「你別走啊,別留我一個人。」我捧著他的臉,哭戚戚地吻他,從臉頰到嘴唇,一遍遍地來回摩挲著。
「求求你了,這回要走也帶我一起。」我可憐巴巴地求他,「行嗎,清和。」
21
酒這玩意兒誤事,我說錯話了。
兩個字一出口,一切都完蛋。
司令府的書房被唐清川砸了個稀巴爛,連蔡綿綿都攔不住。
唐鬱嚇得哭,唐清川指著他喝道:「不許哭,都是你爹搞出來的事兒!」
他自顧自地罵著:「造孽啊,真是造孽!他唐清和一輩子和老子不對付,怎麼偏偏女人這樁事上……」
是造孽,全員替身,誰都沒逃掉。
蔡綿綿聞言去捂他的嘴:「你小點聲,孩子在呢。
」
等他發洩夠了,我酒也徹底醒了。
唐清川坐在我面前,拷問似的與我四目相對。
不等他問,我先開口:「許你抱著我叫綿綿,就不許我吻著你叫清和嗎?」
「對,不許,就是不許!」他惡狠狠地咬著牙,「老子是州官,老子可以放火,但你不能點燈!」
行,那我低下頭,無言以對。
「你幹嗎白久霜?是你對不起我,你怎麼又擺出這死魚樣?」他非要扳著我的臉抬起我下巴,「你說,你來這兒到底是想做什麼?」
「你綁我來的。」
他沒什麼耐心,大著嗓道:「說實話!」
「殺你,報仇。」
「什麼仇?」
我抬起頭,灼灼地盯著他:「司令做過什麼,司令自己明白。」
「你是說,老子殺了自己親哥哥的事兒?」他咧著嘴,說起來輕巧又戲謔,卻說得我目眥欲裂。
「好,好,白久霜,你先別生氣。你氣壞了身子,最後也還是得老子疼。」
唐清川輕輕摸了摸我的臉,算作逗狗似的安撫,
「是,你是知道,大哥死于我的手。可你知道嗎,他留洋期間,是如何與洋人勾結,如何沆瀣一氣,又是如何置百姓生死于不顧。我若不殺他,他做了司令,千萬黎民又是數十年的水深火熱。這些你知道嗎?」
我當然知道。
所以啊,所以明明有那麼多次機會,我卻遲遲下不了手。
我只能嘴上啐他:「弑兄之罪,你死後定入地獄。」
「對,老子是罪該萬死,是死後下地獄。
但只要還活著,老子就得殺了他,就得自己當這個司令!」
唐清川站起身,抬起雙手,許久才落到我兩肩,輕輕幫我理好一頭亂髮:
「白久霜,老子比他是個東西,是個男人。如果當年是我,我不會為了狗屁父母之命丟下你走,留你一個人。倘若有一天我拋下你了,定然不是不要你,只能是為了讓你好好活。」
他的話像是一個預告,叫人隱隱地心下不安。
22
那之後,唐清川好幾日沒再出去。
他收走了我身上一切可能傷害到他,或傷害到自己的東西。
不與我在一處時,他甚至把我銬在床頭。
「受著。」他和我說,「養只老虎在邊上,我可不得小心著點。你那槍法,誰能挨得住啊!」
夜裡,他就總和我纏在一起,像是要榨盡我精血似的。
「怎麼辦,白久霜,我好像愛上你了。」他屢屢這樣和我說,哪怕他說這話時,我的一隻手還被他緊緊銬著。
他品嘗著我失去自由的身子,陶醉其中:「不是愛一個像她的人,而就是愛上你了。」
我一如既往冷言冷語:「別騙自己,你不愛我。不過是因為現在的我,才像那個做你嫂嫂前的蔡綿綿。」
我沒說的後半句是,而後來的蔡綿綿,才更像本來的我。
畢竟,她是在刻意地學習。
嬌嗔、索取、矯揉、肆意,那些本就都是用來引誘男人的把戲。
「放屁,老子就是愛你,就是愛你就是愛你,你根本什麼都不懂!」
唐清川不許我否定,他氣惱地壓住我,看著我毫無表情的一張臉,罵了聲娘,「老子是瘋了,才愛你這死魚,愛你這滿腦子是唐清和的女人!」
我斜過頭去不看他。
他就伏在我身上,又是一通蠻勁。
「叫出來。」他逼我,如同我們第一次歡愛時那般,「你叫出來,讓我知道,你也能因我而快樂。」
鬼使神差地,我順從了。
完事後,他幫我解開手銬,緊緊地將我抱進懷裡,沉聲在我耳邊說:
「你知道嗎久霜,你知道嗎,你真讓人無能為力。」
「想起綿綿,我知道怎麼為她安置一切,房產、金錢、船票,所有的我都能為她準備好,讓她無憂無慮過好下半生。」
「但想起你,我不知道怎麼做。放你走,我是真捨不得,可把你留在身邊,讓你置身危險,我又做不到。」
我靜靜聽他說著。
「老子現在才知道揣著個寶貝是什麼滋味,當真就是捧著怕摔了,含著怕化了……」他摸著我的臉,「早知如此,當初不請你這尊佛回來。」
說到這句,他哂笑道:「不過現在想來,與其說我看上了你強取豪奪,倒不如說,是你處心積慮暴露在我眼前,就為了有朝一日殺我,對嗎?」
我不答他,簡單明瞭的事兒,犯不著說出來。
23
其實,外面發生了什麼我都知道,也知道這樣的日子不會久了。
每天的報紙我都看,我看到很多日本人的消息,看到那些模糊照片中的尖刀和屍體,看到那些文字演化成奮力而無奈的呐喊。
看到槍林彈雨,戰火滔天,而這些,唐清川同樣盡收眼中,並無法坐以待斃。
他近日很反常。
整個司令府都不對勁。
他又恢復了不怎麼回家的狀態,蔡綿綿也神神秘秘地把自己關在房裡,不知道都在做些什麼。
她給我拿來了那套珠寶,舞會前曾親手幫我戴上的那一副。
「物歸原主。」蔡綿綿遞過來,「那日你問淵源,我才明白。清和這麼喜歡它們,大概是因為你曾戴過吧。與其說是送我的禮物,不如說是一套裝飾,好把我打扮成更像沈扶桑的模樣。而如今,我是真用不上了。」
我收下了,可真正該物歸原主的東西,她不肯給我。
所有人好像在按部就班地過活,卻又總像行將就木的掙紮。
唐清川不回來,陳副官倒是跑得挺勤。
有一日,他來府上接我,說是唐清川的吩咐,怕我在家裡待悶了,接我去學校轉轉解解乏。
我將信將疑地上了車,剛坐穩,車就飛快地行駛起來。
我立刻警覺:「去哪兒陳副官,我們這是去哪?」
「碼頭。」他也不瞞我,「開戰了,日本人打進來了。司令不放心白小姐繼續待在這,讓我護送您離開。放心吧白小姐,錢財住所這些司令都安置好了。人太多了招眼,只能您單獨走。」
難怪,這些日子,蔡綿綿是在收拾行李。
「停車。」我喝道。
陳副官意料之中的不加理會。
「我說停車。」
他開得更快了些。
「唐清川沒資格替我做決定,他還欠我一條命呢!」
說罷,我不顧陳副官的高速行駛,打開車門跳了下去。
24
「老子讓你護送她安全離開,沒讓你把她弄出傷,更沒讓你把她整這兒來啊!」
指揮部中,醫生給我上著藥,唐清川在門口訓著陳副官。
「沒辦法司令,白小姐她,她跳車。我怕她再做出什麼事兒,萬一真傷著自己了,您可不得心疼。」
「真傷著自己?你什麼意思,她現在這就不算傷嗎?」
唐清川揪著他耳朵一路把他拖進來,指著我破了層皮的胳膊,「來,你看看,你給老子好好看看,讓你送個人,你給老子整出這麼鮮血淋漓一大口子!」
明明就是方寸之間蹭破了皮,血都沒出來幾滴。
「報告司令。」說著話,門外進來一個士官,「一切已準備就緒,等待司令指令。」
「知道了。」唐清川的臉沉下來。
我這才開始認認真真地打量起面前他這一身裝扮,他是要上戰場。
「幹嗎,嚷嚷著要見我,怎麼見了我就啞巴?」唐清川蹲在我面前,溫言細語,全然是寵溺,沒有半分司令的威儀。
「能不走嗎?」
「你是說你,還是說我?」
「仗要打,我攔不住你,也不可能攔你。」我低頭道,「只是,你還欠我一條命呢。」
唐清川聞言立刻捂住腰間的槍,調笑著:「怎麼這麼執拗,還想殺我呢?」
我笑了,我第一次這樣沖他笑,盯著他,就只沖他笑。
笑著笑著他也笑起來,我們相視相望,我們心照不宣。
「司令,得快些,來不及了。」直到,陳副官在一旁提醒。
「知道了,就你話多!」唐清川連踢帶踹把他轟出去,又轉而看向我,「好,久霜,你不走,你不想走就不走。」
我點頭。
「久霜啊……」他看著我,無比不舍地摩挲著我的臉頰,「你知道嗎,那日,你說你要殺我,我就在想,要不把槍給你得了。讓你抵上我的胸膛,和你說你要是真捨得,要是非得報仇,你就開槍,你就把我崩了。我賭一把,賭你對我有情,賭你下不去手。就算賭輸了,我也是牡丹花下死,留個風流故事,算不枉此生。」
我依舊點著頭,任憑他說,任憑淚水滾燙地爬滿雙頰。
「但是久霜,唐清川可以賭,可唐司令賭不起。如今賊人在蠶食我國土,我是錚錚男兒,麾下有百萬雄師,身後是千萬百姓。我不能死在你槍下,我必須要死在沙場上,必須要在那些賊寇的炮彈中流盡最後一滴血,才算完滿。所以久霜,我很抱歉,我真的很抱歉,我不能遂了你的願……」
「嗯。」我木木地,一下一下地啄著腦袋,「我知道,我知道了……」
「沒事的久霜,別哭,你還有機會呢。你相信我,我此去,除非戰爭結束,國家勝利,否則,我絕不可能苟活于世。而若有幸,能等到凱旋,我必親手將這把槍交到你手上,到那時,再把我的命還給你。
」
我死死地盯著他,生怕一晃神人就沒了似的:「唐清川,那你記得你今日所諾。我要你答應我,無論何時,你都會竭力為我留下這條命,不會就義,不會赴死。」
唐清川無言地在我額頭留下輕輕一吻,他眨了眨泛紅的眼,努力綻開一個笑,卻什麼也沒答我。
陳副官又進來催了一次,唐清川終于點點頭。
他轉身離去,沒再回頭看我一眼。
仿佛只要看了,他就走不動了。
相識一場,到終了才知道,他堂堂唐司令竟吝嗇如斯。
性命捨不得給我,承諾也捨不得。
他根本,沒打算活著回來。
25
蔡綿綿母子走了,偌大的司令府到頭只剩下了我一個人。
我再也不看報紙,那種想看,又生怕看到什麼的情緒,我真是受不住。
外面四處是逃散的流民,是難熬的饑荒。
我又穿上白色旗袍,回到了學校。
流彈肆意地炸著,我卻想,這樣也好。
念及如此的我,唐清川也許會更奮勇,又也許,會更惜命吧。
如此的時光過了幾年,有一天,從前司令府的一個衛兵,送來了一個盒子。
我打開,裡面是滿滿登登的信件,熟悉的字體,熟悉的語氣,每一封的起始都是「扶桑」,落款都是「清和」。
「誰讓你送的?」
「唐司令。」
我喜出望外:「他回來了?」
「不是,是司令一早備好的。」他面露難色,抬眼看了看我,深吸一口氣還是道了出來,「唐司令去打仗前,曾把這個交給我。
他說,他也自私,也嫉妒,雖然找大太太要來了這些,卻遲遲捨不得給你。可若有一日,他死了……」
「什麼?什麼死了?」
此時的無聲,就是一切的回答。
26
那晚,我坐了很久。
然後點了個火盆,將那些陳年的信件付之一炬。
翌日一早,我推開窗。
外面落了一地繁霜。
全文完。
作者:小喬
來源:知乎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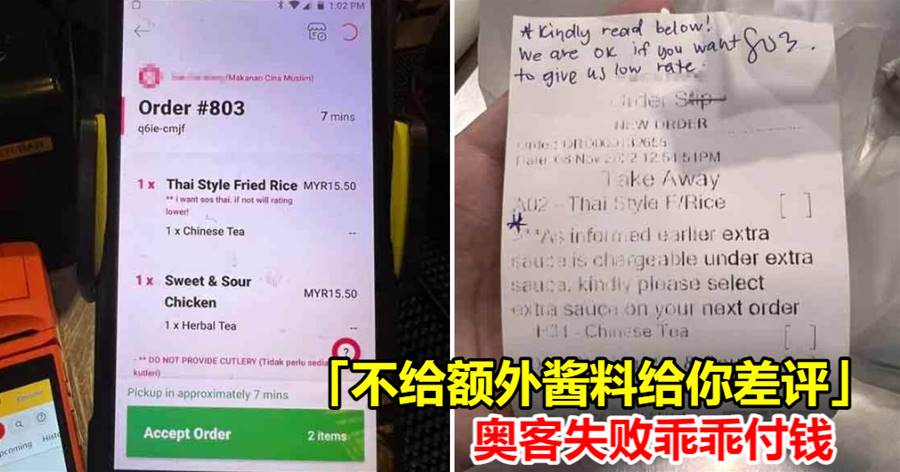

代表者: 土屋千冬
郵便番号:114-0001
住所:東京都北区東十条3丁目16番4号
資本金:2,000,000円
設立日:2023年03月07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