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24
我醒來時,已經將近黃昏,意外看到方景文竟然在階下,像是等了我許久。
「殿下!」
他隱忍怒氣,「殿下可是在耍我?」
我起身整理衣裳,不緊不慢道:「將軍這是何意?」
「先皇賜下的土地,均是皇家土地,私自買賣者,杖二百,投入監獄。殿下的第一個條件,我根本不可能達成!」
他眼中怒火熊熊。
「是啊,我是在耍你。」我乾脆承認了。
「你!」他氣得忘記敬稱。
「可將軍,不也是在第二個條件上,玩弄于我嗎?」
「可順序上!公主耍我在先!」
「我可沒騙你。」
我走到他面前,平視他。
意味深長道:「只是時機還未成熟罷了。」
他追問時,我卻絕口不提。
25
「公主難道想追著我不放,因此提出這種要求?」
他話鋒一轉,冷冷道:「我可要提醒大公主,我心中只有……」
「知道了知道了,我知道去寺廟禮佛時你被刺客圍攻,身受重傷,是仁熹細心照料你,讓你非卿不娶!行了,不必重複,你一定會如願以償的,這樣可以嗎!」
我動了點怒。
「你、你怎麼知道?」
「你管我?」
「更何況……」我心念一動,拉過一直很安靜的男子。
「沒有你,我也照樣活得自在,這是我的面首,醜奴。」
方景文看看醜奴的臉,又看看我。
嘲諷道:「公主真是……好奇特的口味。」
「這就不勞將軍費心了,接下來就是我和醜奴的事了,你說是吧,醜奴?」
我以為的應答聲並沒有出現。
「醜奴?」
我僵著臉,語帶催促。
他的目光卻直直放在剛剛走過來的女子身上。
我看過去。
是仁熹。
「回殿下,草民,拒絕。」
他低啞的聲音,像重錘一般,擊打在我心上。
我不敢相信,捂著胸口後退幾步,竟然直接坐在地上,儀態盡失。
26
醜奴不安地來扶我,被我一把揮開,「滾!」
「好,好,好,好得很!」
我自己爬起來,伸手抽出方景文腰間的鞭子,就要去抽他。
孰料仁熹忽然跑來擋在醜奴面前。
我硬生生停手。
「阿姐莫生氣,這侍衛不識好歹,阿姐乾脆把他給我罷。」
原來救我,照顧我,忍受我的脾氣,並不代表他愛我。
醜奴的目光一直跟著仁熹,一向沒有感情的眸子滿是執著。
原來,沒有人會喜歡我。
喜歡我這個孽種。
我的目光慢慢掃過驚呆的方景文,笑得完美無缺的陶仁熹……
以及那個,從來沒被我正眼看過的醜侍衛。
好,好,好。
我艱澀道:「妹妹既然喜歡,帶走便是了。」
27
「你跟著我做什麼?」
我回頭看著方景文。
他搖搖頭,欲言又止。
「你那是什麼表情,可憐我?真是稀奇。」
我拿起一壇酒,揭開封紙。
「這種表情,我看得多了,你也和他們一樣,在背地裡嘲笑我。」
「我沒有!」
他急道。
「那你就喝了這酒。」
我拎起一壇酒,他下意識接過,神色猶豫。
「你就是看不起我,我知道!」
「我!」
他一急,直接大口大口灌下去,被嗆得連連咳嗽。
我大笑起來。
28
暮色四合,各院子依次亮起燈。
我們坐在房頂,酒過三巡。
「你知道嗎?母后當時就這麼——」
「砰!」
一個被喝光的酒罈咕嚕咕嚕滾下去了。
「就這麼一聲,死了。」我說。
我沒發現自己在流淚。
方景文已經微醺,臉頰泛起淡淡紅暈,他一直在沉默。
「我敬你方家滿門忠烈,于是聽到你昏迷的那一刻,我想,仁熹不願嫁,我嫁就是了。」
「她有她的幸福,誰想下輩子守寡呢?」
「我嫁給你,不賺,但也不虧。」
「公主真是……時時惦記著金錢啊。」
「若無愛,便謀財……你什麼表情?」
我警惕道。
「憐惜往往會發展為愛,你不要喜歡我。」
他安靜地看著我,像是之前從來沒有認識過,卻未頂我一句「自作多情」。
半晌。
他的聲音輕飄飄地,散在風中。
「……」
「嗯。」
29
宿醉過後,一個消息傳遍京城。
大業的宿敵在連吃敗仗後,終于決定求和。
他們派遣的使臣終于在今日抵京,帶來了牛羊、金銀,父皇龍顏大悅,決定在宮中設宴三日。
在姨母的努力下,我終于得以入宮,在宮中暫住,一直到宴席結束為止。
夜晚,大殿燈火通明,我與仁熹坐在一起,對面坐著唯一的皇子,陶飛白。
他面色蒼白,一看便是長期服藥的樣子。
我知道是母后下的毒,宮中對此事諱莫如深。
飛白倒是對我還算和善。
我對他點點頭。
他看到仁熹面前的酒水,轉頭吩咐宮人幾句。
不多時,仁熹身前的酒水便被換成溫熱的,她淺啜一口,對陶飛白露出依賴的笑。
飛白很寵仁熹,這是共識。
30
夜深了,歌舞也演過幾旬。
使臣起身,恭維父皇,直讓他哈哈大笑。
之後,使臣道:「臣今日來到大業,還帶來了可汗的一個請求,不知陛下……」
父皇豪爽地揮手,「講!朕能做到的,一定滿足!」
使臣拱手道:「可汗久慕中原文化,欲……迎娶一位陛下的珍寶。」
父皇酒喝得太多,意識昏沉,「嗯?什麼……珠寶……」
但其他人都聽懂了。
當今陛下,只有兩位公主。
大公主已然出嫁,因此……
我看向仁熹,她的小臉已然白了。
31
氣氛凝滯。
秦謹豁然站起來。
方景文緊隨其後。
陶飛白捏緊了手中的筷子。
父皇打了個酒嗝,在大殿裡,卻顯得響亮。
他清醒了,臉色也變了。
含糊道:「再議、再議,朕乏了,都散了吧。」
隔著遠遠的大臣,我看到秦謹懷疑的目光,悠悠落在我身上。
32
仁熹一天未進食。
我來勸她,絲毫沒有成效,只能無奈離開。
在殿門口,我遇到了來看仁熹的秦謹。
我對他點點頭,正要和他擦身而過。
他卻拉住我,問。
「殿下早就知道?」
「什麼?」我反問。
「和親……」他深深望進我眼中,像是要把我看穿。
「秦大人說笑了,我怎麼可能知道這些?我只不過是一個不受寵的公主罷了。」
他眼中懷疑稍稍退去。
「打擾公主殿下。」
我卻不肯輕易放人。
「秦謹,」我把恨意咬碎,任其一絲一縷地從嘴裡流出來,化作傷人的毒液。
他停住腳步,回頭,不見有情。
「你說喜愛澄泥硯,我散盡千金去求;你喜愛吳山的畫,他脾氣古怪,我便軟磨硬泡三個月,得了那幅你愛不釋手的畫;你喜歡仁熹,我替她出嫁……秦謹,我哪裡對不起你?」
「可你見到我,只是問我這麼荒謬的問題。」
「難道只有我將心剖出來,血淋淋地捧給你,你才會信我?好。」
我拔下簪子,抵在右胸。
「陶仁姝,你瘋了!」
「我是個瘋子,可因為一首詩便愛上仁熹的你,是什麼,傻子?」
他握住我的手,緊緊地,連同那只冰涼的銀簪。
簪子上的那點光亮,投射在他滇黑的眼眸中,恍惚是個絕情到底的眼神。
是崩前的雪山。
是山雨欲來前夕,小樓上飄飛的重重帷幔。
恰似那一圍纖長的眼睫。
庭院深深,深幾許?
「太子是未來的皇帝,我畢生夢想,是成為丞相,一人之下,萬人之上。」
「仁熹是他寵愛的妹妹,而你不是。」
「這話我只說一次,陶仁姝,你不會不懂,莫要再裝了。」
33
天生的野心家。
我收起那幅要生要死的模樣,冷笑一聲。
擅長厚黑學的翰林,到底沒有方景文那種頭腦簡單的武將好糊弄。
「那你對仁熹呢?都是裝的麼?」
我問。
他很快收起對我變臉的驚疑,噗嗤笑出來。
「我以為公主懂的,這深宮十八年,公主竟然還有這麼一絲天真麼?真心無論重不重要,它只是不值一文。」
「是啊。」
我也跟著笑。
「若我也有一個疼我的皇弟呢,你是否會轉過來愛我?到時候我的真心,是不是很值錢呢?」
「待價而沽,公主若是愛財,這個道理豈能不懂?」
將真心化作武器,踩著它達到目的,這是秦謹所信奉的,他也確實做到了,他將仁熹哄得神魂顛倒,讓陶飛白滿以為得到一員能在文臣裡一呼百應的臂膀。
我就是不願用,不敢用。
才扭扭捏捏,藕斷絲連。
才將一顆心劈成數瓣,表面上愛著這個翰林,卻存著拉攏他的心意;表面上敬慕這位將軍為國效死,暗地卻勾著他,甚至……騙著他。
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到頭來,我好像已經將它弄丟了。
愛過的,誰不愛這種男人,可自他毫不猶豫站出來,拒絕讓仁熹嫁給方景文時,我便知道,他不再屬于我了。
34
「好,那麼此刻站在你面前的,不是瘋狂追逐你的仁姝,而是大業的長公主。秦謹,本宮問你,若本宮真的有一位視我如珠如寶的皇弟呢,你是否願意……」
我沒有明說。
「臣願。」
他靜默一刻,像是窺見甚麼引而不發的、神秘的苗頭,愉悅地笑起來。
「我的……殿下。
」
「好,很好。」
這就夠了。
35
我知道仁熹不會想去的。
飛白也不會讓她去。
可父皇沒有不答應的道理。
送一個公主,保三十年和平。
何其偉大的功績。
尤其是他這種,登基以來,毫無建樹的庸碌君主。
他登基第二年,蠻族來犯,他壯志淩雲,禦駕親征,卻被人一劍射過頭髮,嚇得屁滾尿流,再也不提上戰場,取敵人首級這種事。
他的正妻,我的母后,卻展現出了令人驚歎的智慧與謀略。
在她的指揮下,大業很快取得壓倒性的勝利。
父皇十分寵愛她,兩人琴瑟和鳴,生下了我。
可母后卻遲遲沒有再生下一位皇子。
說回父皇,他一生建樹不多,而大業的死敵求和,這是我他的祖輩沒有做到的事。
而他卻做到了,豈不令他揚眉吐氣,因此犧牲一個女兒,實在是,
小事罷了。
36
秦謹在禦書房前跪了一天,父皇不肯鬆口將仁熹嫁給他。
他就是這種人,即使仁熹是他最喜愛的女兒。
我知道有人坐不住了。
我出殿,和陶飛白打了個照面。
他輕咳幾聲,「皇姐這是要去哪?」
我微笑:「裡面悶,出來逛逛。」
飛白不疑有他。
今日是宴會最後一日,裡面還是如此熱鬧。
群臣都知道,皇帝今晚要答應使臣的要求。
仁熹沒有出席,大家心照不宣地略過了。
陶飛白的身影消失在視線後,我疾步離開,很快走到一處宮殿。
「殿下,你喝醉了……」
「謹哥哥,幫我……」
「臣不能……」
「只要……我倆……父皇會給我們賜婚……」
「我不想和親,求求你……」
「我……」
「求你,謹哥哥……」
我揚起嘴角。
門口只有一個人把守,是醜奴。
我越過他,推開門,[呻·吟]聲夾雜著熱浪撲上來。
出乎意料,醜奴並未攔我。
仁熹像是用了藥,攀附在秦謹身上,羅衫半褪,神志不清。
秦謹衣冠淩亂,神情卻是玩味。
37
看到我,他輕笑:「公主來了?」
「是啊,這出好戲,什麼時候落幕呢?」
「那就要看長公主的誠意了,公主打算甚麼時候將計畫和盤托出呢?」
仁熹神志不清,不知道我們在講什麼,只是難過地扭動身軀。
「好熱,救救我……來人……」
「待你做完這齣戲,現在,可以走了。」
秦謹順從地放開仁熹,含笑問:「公主看中了哪個倒楣的侍衛?」
我哼道:「作惡多端的,醜的。」
話落,一個中了藥的醜陋侍衛被扔進來,他身材肥碩,滿臉橫肉。
「公主真是狠心那。」
他裝模作樣感歎。
「一報還一報罷了。」
我同樣回以假笑。
「這只是個開始。」
38
那侍衛撲上去,而殿門也緩緩闔上,掩住那樁惡事。
我對著朱紅的柱子出神,良久喃喃:「鵝兒唼啑梔黃觜,鳳子輕盈膩粉腰。」
「這是二公主當日寫在紅葉上的詩句。」
「深院下簾人晝寢,紅薔薇架碧芭蕉,這卻是我未寫出的下聯。
」
「原來是大公主所寫,如此,也不算奇怪。」
他拊掌道:「此詩意趣難得,難怪此後我再沒見到仁熹有如此佳作,原來是個文抄公。不知公主何時能贈臣一片紅葉呢?」
他言談之前,竟是迅速將仁熹拋在腦後,言語間,向我調起情來。
此等冷酷心境,真是讓人心驚。
我不置可否地笑笑。
39
我回到宴席,恰逢飛白滿臉擔憂,道仁熹不吃不喝,他怕出事,請父皇一同去看看仁熹。
「我也去。」
父皇看了我一眼,點點頭。
我們三個人,身後跟著些大臣夫人,一路來到仁熹宮中。
飛白上前一步:「仁熹,父皇來看你了……你莫要……你!你是誰!」
他面色大變。
我看到父皇皺眉,快步上前推開門。
裡面的一切,明明白白地展現在所有人面前。
仁熹正抱著一個醜男人,在床上翻滾。
「!」
不知是誰先低喊一聲,只見為首的皇帝,竟然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
40
亂了,都亂了。
備受寵愛的二公主陶仁熹,竟然如此放蕩!
太子直接砍了那個侍衛,又殺了一批宮人。
只是,大臣殺不得,大公主殺不得。
這樁醜事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,發酵了。
趁宮中一片混亂,陶飛白處理局勢,我走到父皇的宮殿。
宮人不敢攔我,我摒退太醫後,殿中只有我們兩人。
我端起藥,扶起他,要給他喂藥。
他看著我,眼含審視。
「兒臣只是憂心父皇龍體,不過喝藥之前,還是先驗驗罷。
」
我不動聲色,道。
我拿出銀針,片刻拔出來後,銀針已是全黑。
41
「!」
他立刻拍掉碗,瞪著地上的碎片喘氣。
「是、是誰要害朕!這藥是誰送來的!」
「回陛下,是、是太子……」
「你說什麼!」我推開太醫,大喊。
「你們快給父皇把脈!」
太醫顫顫巍巍上前,俄而猝然大驚。
「病入膏肓,油盡燈枯!陛下,怕是、怕是沒有多長時間了!」
「為何之前從未診斷出來!」
我厲聲道。
「回殿下,這毒日常蟄伏,只有在受到刺激時,才會被催化發作,露出端倪……」
「只要再喝下最後一副藥……就會、就會……」
父皇眼睛猩紅,「會怎樣!」
「會……立刻……暴斃。」
我臉色一變,指著地毯上藥湯的殘渣,「這、這莫非!」
太醫令看到地上的藥汁,爬過去舔了舔,「陛下,正是此藥!」
他癱倒在地上。
42
「好!真是朕的好兒子,如此迫不及待!朕要廢了他!」
他忽然想到,他沒有第二個兒子了,不由得鬆開手上空白的聖旨,頹然倒下。
我忽然跪下,重重磕了三個響頭,額角很快滲出血絲。
「姝兒,你這是做什麼!」
父皇大驚。
「父皇,」我哽咽道,「母后沒有和侍衛私通!這是我不久前從母后嫁妝中找到的,請您過目!」
那是一幅,用血寫成的,萬福圖。
由于時間久遠,血跡變得乾枯,像一片褪色的曼殊沙華。
「這是母后死前一直在寫的,她說,要寫好,再給父皇,怎麼可能轉眼就和侍衛私通呢!」
「父皇,母后,冤啊——!」
父皇哆哆嗦嗦地接過去,忽然流淚。
「你為何一直不說?」
「兒臣,不敢。」
「是誰幹的!」
我搖搖頭,緊緊閉嘴。
「是張柳幹的,是不是!」
張柳是我的姨母,現皇后的名諱。
我臉色一變,深深伏在地上,肩膀聳動。
我不是在哭,我只是……難以抑制臉上的恨意。
父皇啊父皇,你慣會裝模作樣。
你本來就知道,母后不可能做出那種事,可你還是……
父皇一連說了三個「好」字,好似一個剛剛得知宮廷隱私的君王,世界陡然在他面前變了個模樣。
呵。
是你害死了母后,我的……父皇。
43
「朕多年只有一子,也是她幹的?」
「兒臣看到,仁熹推了臨盆前的趙美人,致其早產。那孩子生下來只哭了三聲,就在父皇懷中逝去了。」
父皇想起趙美人,臉色複雜。
「趙美人身子弱,早產幾天後便去了,但,您的孩子,並沒死。」
「他是位皇子,我力量微薄,只能將他遠遠送走。」
「那他現在在何處!」
我不語,將目光轉向殿門。
一個人出現在那裡。
腰間配侍衛刀,臉上有猙獰傷痕。
是醜奴。
44
「我那早死的皇兒?他怎麼會還活著?」父皇爆發出驚人的力量,死死拉著醜奴的手,神情癲狂,顯然是迴光返照。
父皇刺破指尖,和醜奴的血和自己的,一起滴入碗中。
「溶了,溶了!」
父皇忽然卻冷靜下來,道:「那時你是在朕懷中去的,這麼多年過去,朕還清楚記得,你腰後有一塊胎記,你過來,讓朕看看。
」
我僵住。
但我不能說甚麼,只能悄悄攥緊拳,任長長的指甲紮進掌中。
我和醜奴之前,並沒有注意,趙美人的孩子腰後,有這樣一個胎記。
怎麼辦?
醜奴一動不動,從容道:「草民身上並無胎記,陛下許是記錯了。」
氣氛停滯,如同過了一個世紀。
父皇笑了:「是,朕記錯了。」
他竟然是在詐我們!
我沉重地吐出一口氣。
我知道,父皇也許並沒不相信,醜奴就是當年的孩子。
可如今飛白要害他,他知自己時日無多,寧願抓住救命稻草般,相信醜奴就是那個孩子。
45
「朕要改立太子,你以後,便叫做陶和衷罷。來人,上紙筆。」
「父皇要廢我這個太子,怎麼不和我說一聲呢?」
陶飛白大步走進來。
父皇平靜道:「孽子,爾安敢來。」
他這副不怒自威的樣子,恍惚是壯年風采,竟將陶飛白嚇得瑟縮一下。
「為何不敢?父皇,你快要——死了啊。」
他拉長聲音,臉帶嘲諷,揮揮手,身後便出現了一隊身著黑甲的侍衛,正是守衛宮闈的禦林軍。
「朕問你,朕身上的毒,是你下的?」
陶飛白爽快道:「是。」
「你小時候,並未中毒;先皇后的事,是你所為。」
「父皇竟然今日才反應過來?誣陷姨母與侍衛私通,是仁熹的主意。將父皇帶過去的是母后,姨母送來的藥湯,只是溫補身體用的,而我假裝中毒,就是為了,再推姨母一把啊。
」
他幽幽歎道。
「你!」父皇被他不知廉恥的模樣激怒,「孽畜!」
「姨母有什麼錯呢?只是母后想當六宮之主,我想做天下之主罷了。她唯一的錯,就是擋了我們的路。」
「皇姐。」他轉向我,「我本來想要一步步來的,可是誰知父皇受到刺激,提前發現了身體上的問題,我實在是被逼得沒辦法啊——」
「咦?父皇手中拿的可是聖旨?方將軍,你去取來給我看看。」
我神色晦暗,看著方景文一步步走近。
他避開我的目光,不知是羞恥還是什麼。
46
「方將軍還愣著做什麼!待我登基,立刻幫你休了皇姐,將仁熹嫁于你!」
方景文動了,他舉起劍,就要將那聖旨砍斷。
「方景文,你要做逆賊。」我平靜質問。
方景文的劍已然逼近父皇,電光火石間,我看到飛白臉上露出志在必得的笑。
就在那一瞬間,他突然蹲身拿起劍,站在父皇身前,是個護衛的姿態。
這突如其來的變故,陶飛白震驚無比,他定定望向方景文,眼裡滿是疑惑。
「方家世代為皇帝效死,絕不參與皇位爭鬥,如今,又豈會為了一個女人——」
我替他作出了解釋。
況且,不久前方景文又得知,心心念念的救命恩人,他付出真心等待之人,其實不是仁熹,而是我。
45
方景文與秦謹不同,秦謹是無情,他卻是個情種,我為此頭疼不已。
那日,我長長、長長地歎了口氣,告訴了他真相。
「對不住了,方景文,不,元寶。」
「元寶」是我當時給他取的昵稱,因為我愛財嘛。
「你叫我什麼?」
陶飛白的眼皮狠狠跳了三下。
「之前你問我,如何知道你和仁熹的緣起,這就是答案。你當時中毒,看不清人,我只能扛著你下山,你可真是太重了。」
我小小抱怨一下。
「你,你,你……」
「方景文,當日我提出和離三個要求,第三個條件,我要你幫我,你肯是不肯?」
「自然願意」
他紅了眼眶。
我滿意了,「多謝你,將軍。」
47
「啪、啪、啪!」
「皇姐真是好謀略。只是你真以為,有了方將軍,你就能轉敗為勝?這醜人是皇姐找來的?難為皇姐了。」
「這是你皇弟,未來天子,不得無禮!」
「皇弟?!這又是你從哪裡找來的?無憑無據,誰信他是未來天子呢?方將軍臨陣倒戈了不要緊,你們上,事成之後,加官進爵!」他沖禦林軍下令。
「他們知道。」我淡淡道。
「誰?你們怎會在此?」
陶飛白看到了朝廷的肱骨大臣們,正一臉複雜地看著這個弑君的太子。
廢話,自然是我。
醜奴,也就是陶和衷,一直站在不起眼的暗處,他悄無聲息地上前,一掌劈暈了他。
大勢已去。
48
父皇此時猛地吐出一口血。
「父皇!」我大驚,撲到他身邊。
「朕……時日無多……來人,朕要寫傳位詔書。」
立刻有宮人上前,執起紙筆。
我心如擂鼓。
終于嗎?
大臣們安靜地、悲戚地看著他。
「今朕年屆七旬,在位六十一年,實賴天地宗社之默佑,非朕涼德之所至也……
朕為奸人暗害,時日無多……陶飛白,流放三千里;張氏,棄屍荒野;公主仁熹,貶為庶民……」
當年害死母后的人,終究得到了報應。
陶仁熹想出毒計,張柳(現皇后)將父皇帶了過去。
還有父皇。
他 明知道以母后的性格,不可能做出這種事,還是裝作被背叛的模樣,裝了一十五年。
他們,都該死。
「茲立……」
終于……
「陶……」
我看了看陶和衷,他正抬手,虛虛摸了下傷疤。
他是那個,和母后「私通」的侍衛之子。
他劃破了肖父的面容,和我籌謀數年,只有一個目的,就是報仇。
49
我和他演戲,讓仁熹恰好看見。
她一貫是愛搶我東西的,方景文的救命之恩是,醜奴也是。
于是我得以將他送到仁熹身邊。
給仁熹下藥,遣走她身邊的護衛。
我這一盤棋,終于到了最後的一步。
陶飛白被廢,父皇只剩下一個選擇。
即使這個陶和衷是假的又如何?左右不過多下點功夫,平息流言。
他登基後,會在某一天暴斃,將皇位傳給我。
我就是大業,空前絕後的,女帝。
這條荊棘之路,再難,我也要走下去。
50
「茲立陶……」
這一瞬間,我想到許多。
從假裝愛慕秦謹,放鬆陶飛白的戒心;到瘋狂斂財,得了個「金銀公主」的惡稱。
我八歲前,無憂無慮,那時候,我想要好多好多人愛我,還想要好多好多錢,讓天下人不再過得那麼苦。
到時候我就站上城樓,將成箱成箱的金銀往下倒!嘿!大家都有錢,就不會有人死啦!
八歲之後,我知道了,被愛是要付出代價的;
有些人,是不配苟活的。
我指著母后的棺槨罵了兩個時辰,回頭便吐到胃袋空空。
我想有人赤裸裸地愛我,想有人愛上什麼也不是的我。
可命運的每件饋贈,均是明碼標價。
那時起,我便不再是公主了。
我的真心呀,它被我弄丟啦。
51
父皇卻不說了。
難道是出了什麼紕漏?
我用灼人的目光看著他,控制不住地流露出急切。
說啊,說啊。
「仁姝,你太著急了,這樣不行。」父皇歎氣。
我悚然一驚,「父皇這是在說什麼……兒臣有何可急?」
父皇接下來的內容,卻將我鎮在原地。
「茲立長公主陶仁姝為皇太女,朕百年之後,祖宗基業,盡皆託付與她,忘眾臣勤勉,事她如事朕。」
「什麼!」
他說什麼?
我愣愣看著他,不敢相信。
52
「仁姝。」他說話已經很費力了,「湊近些,讓朕看看你。」
「真像啊,你和你母后。」他喃喃道。
「一樣地無畏、悍勇、堅韌,認定一件事,再難也要做,敢冒天下之大不韙。朕承認,朕怕了,沒有男人想要被女人爬到頭上,更何況,朕是九五之尊。」
「之前滴血認親的水,你做了手腳。
趙美人的皇子,早已死了,這些,朕都知道。你想騙朕將皇位傳給他,再由他傳給你,是不是?」
「你小時候多天真,你想均貧富,想讓所有人都過上好日子,呵,多天真呐。」
「可仁德,是君王最重要的質量。」
所有都被撕破了,赤裸裸地放在明面上。
「您殺了母后,因為她比您出色,他們陷害母后時,您順水推舟。」
我恨意洶湧。
「您讓我這十年,時時烈火焚身,可我本來不該是這樣的!我是您女兒,我是您女兒啊!我也想找一個愛我的人,可我現在,已經不會愛人了!」
我太委屈了。
「我只是……一個女子啊。」
我喊到嘶啞,像是將這些年積壓的委屈一股腦發洩出來。
我恨不得把所有隱秘的籌畫扔出來,讓它們在烈日下被曬得滋滋作響,散發出令人作嘔的惡臭,傷害所有人。
本不該,本不該。
53
「好,好!」
他竟然大笑起來,「這就是朕要的,恨!」
「仁姝。」他的大掌放在我頭頂,輕輕摩挲,像尋常父女間的溫存。
「我是個庸才,若非生在皇家,恰巧做了這個皇帝,我或許連你母親都高攀不上。」
「我一生嫉賢妒能、庸碌醜陋、毫無建樹,被匈奴耍得團團轉,被一劍射頗了膽。」
「但我一生中做過最正確的事,也許是養出了你這樣的一匹狼王。」
「我……」
我張張口,喉頭堵塞。
「仁姝,抬頭看看父親。我問你。
」
我怔怔看著他。
「第一,你仍想讓天下百姓過上好日子嗎?」
「是。兒臣第一步,便是將歷年攢下的銀子拿去買皇田,將其分給百姓耕作。」
「好。第二,你還恨我嗎?」
他眼中有種希冀的光。
54
我眨眨眼,那裡並沒有眼淚。
「父皇,是你殺了母后。」我恨聲道。
他難堪地別過頭去。
「你知道?你確實應該知道的。你從小就聰慧。」
呵。
他咳出一大口血,顯然是油燈枯盡,斷斷續續問出最後一個問題:
「仁姝,你可做好準備了嗎?」
「準備踏上這一條荊棘之路,你會遇到我這樣的男子,嫉賢妒能,看不起女子;在你母后被誣陷之時,順水推舟,冷眼旁觀,只為了找回自己的尊嚴;你會被老學究指著罵,顏面盡失,像我年輕時一樣;你再也不能隨心所欲……」
「你走的這條路,前不見古人,後不見來者,一路猛獸環伺,個個對你虎視眈眈,你怕嗎,仁姝?」
「我不怕。」
「怕也不成了。」他呵呵笑起來,喉嚨似破風箱隆隆作響。
「朕想多教你些,可終究是不成啦。」
他喃喃道:「抱歉,仁姝,要將你一個人……留在這裡了。」
他笑著闔上眼,放在我頭頂的手掌失去了力氣,無力地落下來。
「且視他人之疑目如盞盞鬼火,大膽地去走你的夜路。」
「姝兒……」
「……莫哭。」
這是他最後的話。
55
我下意識抓住那只垂落的手,無意識喊了一聲太醫。
後來我忽然想到,給他下的毒裡面,也有我的一份。
我站起來,跪久了膝蓋酸痛,和衷上來扶住我,走出宮殿。
「陛下,看看您的臣子們。」
我環顧他們悲戚的面孔,眨眨眼。
空中飄起細雨,我伸手去摸臉頰,卻摸到一片潮濕。
難道我哭了?
不,我沒感覺到眼角濕潤呐。
我笑著回頭對方景文道:「方將軍,這雨真是奇也怪哉,怎生都飄到本宮臉上了。」
宮女怯生生道:「陛、陛下,您哭啦。」
「不可能,我有什麼可哭的?這雨真是邪了。」
和衷握住我的肩膀,把我按在他懷中,我嗅到淡淡的皂莢香味,不知怎的起了好勝心,強調:「我、我真的、真的沒哭。」
「我知道。一定是這雨太擾人了。」
他溫柔道。
「對。就、就是。」
我抽噎著強調。
「好。」
他低聲應答著,一遍一遍,不厭其煩。
56
「和衷,你要走?」
臉上有疤的男子應了聲。
「我們原本的計畫是,我登基後暴斃,傳位于你。但先皇直接封你為新帝,我自然沒有留在這裡的理由。」
「可、可我!」
「你什麼?」
「我,我對你!你……你知不知道……」
「那只是依賴,姝兒。」
「我我我……」我急得團團轉,卻不知道該如何將他留下。
「我只是要擺脫這個皇子的身份,會再回來的。」
「何時?」
「陛下選妃之時。」他摸摸我的烏髮。
「也許那時,陛下便能夠看清您的感情了。
」
「……好。」
57
方景文纏我許久了,我遣人送去和離書,他不肯簽。
後來他鬆口了,同意與我和離,但要見我一面。
我允了。
「人也見到了,將軍簽字罷。」
「我不。」
「朕的三個條件,將軍都做到了,為何不願意呢?朕曾經問你,若你後悔了呢?你不屑以對。那麼現在……」
「不。」他忽然想起了什麼,「無人敢買賣皇田,因此公主提出的第一個條件,恕臣無法達成。」
他好似遺憾極了,瞳仁中卻躍動著一團火。
「不,別人不敢買,本公主卻能。」
我拿出一張匯票,「這是朕這些年攢下的,打賞、嫁妝、母后的嫁妝……林林總總加起來,正好是十萬兩,朕的積蓄,全部在這裡了。這些年,朕背負貪財駡名,這名聲錢,將軍可要收好了。」
「原來陛下說時候未到,是這個意思。」
他聲音嘶啞,活像被砂紙磨過。
58
「陛下為何任由陶仁熹誤導我?讓我以為、以為……」
「哦?若我一開始承認,你便能愛上我了?」
「是!」
「哪怕邊關射向你的那一箭,是我命人做的呢?」
「是……什麼?」
「你沒聽錯。」我自顧自道,「我為的就是嫁給你。本來我看好秦謹,可他追著仁熹,我沒辦法,只能讓你受傷,以沖喜的名義嫁給你。」
「仁熹不願嫁給一個廢人,秦謹不願讓她嫁,于是——」
「我站出來,嫁給你,朝堂之上,板上釘釘,便是陶飛白也沒有反應餘地。
」
「這樣的我,是你想要的嗎?」
「我要。」
我詫異地看他,情癡真是不能惹。
「哪怕和親的事,是我促成的呢?我買通人,告訴單于大業的二公主有多麼漂亮。」
「二公主和我無關。」
「哦?」
「若我告訴你,這一切的一切,都是我的一盤棋呢?」
「嫁人便不用去和親,于是這個人只剩下仁熹,她不甘心,想與秦謹生米煮成熟飯,孰料我已然將他策反。我與和衷做戲,將他送到仁熹身邊,她慣愛搶我東西,這下卻是開門揖盜了。」
「聽到這裡,你還敢愛嗎?」
59
「有何不敢?」
他忽然笑了。
「陛下,我在邊疆十幾載,朔風吹拂,練就這麼一副厚面皮,我見過無數殘肢,見識過種種醜惡,這些算得了什麼呢?我方家護佑國土,是祖訓,是累世理想。」
「我一直在想,除去這身甲胄,我還有什麼?」
「我執著追尋的那個人,是否只是幻影?」
「陛下,您救了我,我以身相許。」
「陛下深謀遠慮,既有心計,又兼手段,比我想象的……那個救我的女子……」
我靜靜看著他,說不上是什麼心情。
「比我想象的,還要堅韌動人。」
他一雙鳳目緊緊盯著我,裡面滿是不屈不撓的火光。
他的額頭輕輕碰了碰我的。
像某種小動物,小心翼翼地貼上來,眼眸清澈,天真、熱情、坦承、忠心。
「愛我罷,陛下。」
「求您。」
60
「臣也想請陛下垂憐,微臣只想做陛下窗外一片紅楓,絕不打擾陛下。
」
「秦相位高權重,何必跟著湊熱鬧。」
好不容易送走粘人的方景文,我頭痛道。
「你既已一人之下,萬人之上,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呢?」
「可陛下曾經也道,非臣不嫁。」
「莫開玩笑了,秦相,你不是曾道,真心一文不值嗎?」
我複雜地笑。
「如今朕再問你同樣的話,這真心,到底值幾個錢?」
我玩味道。
「陛下,真心,不名一文。」
他依然堅持。
「陛下要許多許多愛,可時至今日,陛下還能分清誰假意,誰真心嗎?」
他不管我的表情,兀自退下了。
「不管陛下是否允我,可君臣之間,互相扶持,共謀國事,百年之後,微臣必隨陛下而去。後世之人,提起秦謹與陶仁姝,無不慨然而歎,我們會一直被並列提起,直至千年萬年。」
「鵝兒唼啑梔黃觜,鳳子輕盈膩粉腰,陛下,一個野心家所剩無幾的真心,全部都在這裡了。」
我沒來由感到一絲倦怠,身上的金紅袞服還未脫下,眼皮已經在打仗了。
我後退幾步,緊緊抱住膝蓋,在權力的中樞,在燒著龍涎香的華麗書房中,沉沉睡去了。
作者:墨棏感卿
來源:知乎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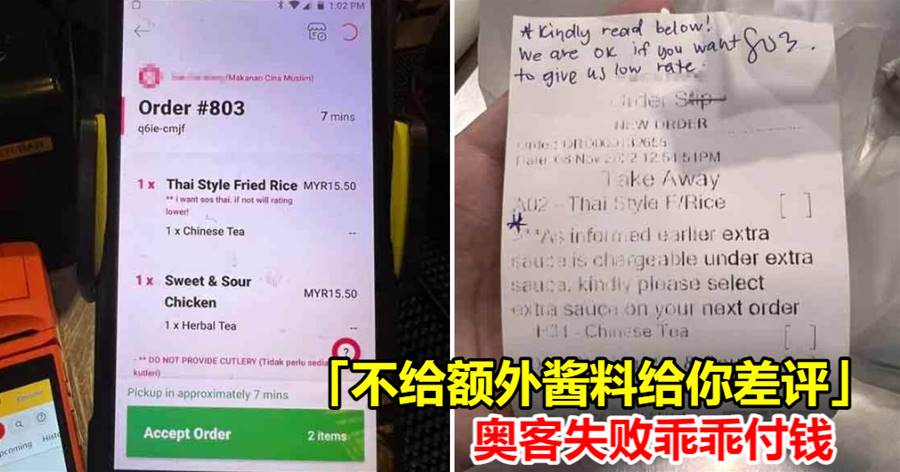

代表者: 土屋千冬
郵便番号:114-0001
住所:東京都北区東十条3丁目16番4号
資本金:2,000,000円
設立日:2023年03月07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