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天不知什麼時候亮了,我撫平自己的裙衫,冷淡道:「既然聖僧送了我一串佛珠,那麼我也送您一件東西。」
樹枝驀地纏住了宗吾的四肢和頸子,不斷絞緊。
更有細弱的枝條刺破皮膚,紮入心脈。
宗吾因劇痛臉色瞬間變得蒼白。
感受到來自靈魂深處宗吾心臟的搏動,我笑出聲來,「疼嗎?當年,我也跟你一樣。」
「槐瑤——」
「閉嘴。」我毫不客氣地打斷了他,譏諷道:「宗吾,你不會以為,我還愛你吧?待我滅了他們,再親手送你去死。」
宗吾輕咳兩聲,「別去。」
我漫不經心道:「求我啊……」
「求你,別去 ……」
他的聲音飽含痛苦。
我輕蔑地嘲笑道:「求我有用嗎?就像當年我求你,到頭來,成了個笑話。」
宗吾試圖抓住我,我手指一勾,樹枝即刻將他死死束縛,壓在牆上。
「別費力氣了,倘若我死了,你也別想活。」
說完,我不再看他,徑直走出了門。
幽深晨霧中,黑衣人早已等多時。
他的身後烏壓壓跪了一群人,看見我,露出驚喜的目光。
黑衣人似乎已經等僵了,很久之後,枯瘦的手掌緩緩劃過耳際。
兜帽滑落,露出一張熟悉的臉。
「妖族長老槐堰,恭迎聖女。」
地上的屍體早已不見,昨夜的斷壁殘桓不過虛像。
妖族後輩不斷自四面八方湧入。
我勾起唇角,抱臂立在門前,道:「老槐先生,好久不見。」
槐堰的目光穿過我,望向門後,語氣和煦問道:「宗吾聖僧一切安好?」
「槐先生說話,什麼時候多出一個拐彎抹角的毛病?」
槐堰倒不尷尬,笑道:「聖女既已恢復記憶,當知道他是最大的變數。當年聖女年幼無知,便也罷了,如今,可不能再錯一回。」
我知道,他們都想讓宗吾死。
我何嘗不是。
可總覺得,輕而易舉地弄死,太便宜他了。
「懇請聖女,處死宗吾。」
「肯定聖女,處死宗吾。」
……
槐堰為首,幾乎所有在場的妖族,都跪在了地上。
他們是怕我,捨不得。
我唇角的笑意泛冷,用輕得不能再輕的聲音緩緩道:「話不是這樣說的,槐先生,少了餌料,魚怎麼上鉤?」
「聖女——」
「好了。」我中途截住他,不容置疑道,「既然你還知道我是聖女,便聽我的,將宗吾的消息放出去,晚些時候,便會有人上門了。」
槐堰眸子閃了閃,默默垂下去,「遵命。」
妖族靈氣旺盛,我坐在槐樹下休養,翹著腿,棕色的佛珠在太陽下熠熠生輝。
我嗤笑一聲,從腳踝上猛地拽下來,揚手就要扔出去。
手在空中卻突然停住,恨恨地盯了半晌,站起來,哐當一聲推開門。
宗吾此刻還掛在那兒,殷殷血跡滲出來。他低垂著頭,眼眸輕闔,聽見動靜,睜開眼,抬眸望來。
我將佛珠狠狠摔在他腳下,惡狠狠道:「誰稀罕你的東西!」
我用了十成的力氣,佛珠撞在地上,被摔得四分五裂。
宗吾眼睫輕顫,用近乎請不見的輕歎對我道:「槐瑤,撿起來。」
我走近他,嗤笑道:「你要本聖女紆尊降貴,一顆顆去撿?」
宗吾的眼中浮現痛苦之色,「那是我——」
「是你什麼?」我發出一聲譏誚的短笑,「你的真心?可真是……太不結實了。」
此話說完,宗吾的臉色猛地浮現蒼白之色,咳出一口血來。
我面無表情地盯著他唇邊的血跡,明明該為此感到高興,卻笑不出來。
插進他心脈的樹枝愈發絞緊,直到宗吾大汗淋漓,我猛地鬆開,啪嗒,一滴淚落在手背上,我後知後覺地抹了把臉,濕漉漉的。
我盯著手心看了半晌,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麼了?
「聖女!他們來人了!」
濕潤的眼睛看向窗外,烏壓壓的人,一如當年。
他們樣貌變了,衣服也變了,但眼神裡的憎惡,從未變過。
「宗吾,你相不相信,世上有輪回?」我輕輕問他,回應我的是無邊沉默。
「這次,我不會選你。」
千年前,妖族遭人重創,休養多年才逐漸恢復繁盛。
如今大戰將起,他們似乎怕妖族反撲,仙家世族能來的人都來全了。
「人比我們多,對嗎?」我站在門前,問從前線打探消息回來的人。
那人凝重地點了點頭,「聖女英明,妖族本就處于劣勢,若非將宗吾扣在手裡,只怕……今夜就要開打。」
「怕什麼!當年怎麼打的,如今還怎麼打。」槐堰冷著臉站在暗處。
那人聞言一愣,「怎麼打?」
我笑道:「自然是布一個誅仙陣,我去祭陣。」
那人聞言大驚,「聖女,你豈不是……」
「魂飛魄散。」我回答地輕飄飄的。
那人繼續問道:「當年……您是怎麼活下來的?」
他這一問,把我問住了,我愣了一陣兒,緩緩笑開:「是槐先生受累,取了我妖丹養著。」
槐堰不說話了。
想來,若不是為了今日,他也不樂意做這件事,還假模假樣地當爹當媽,把我拉扯大。
槐堰轉移了話題:「聖女,少則今夜,多則明日,這一戰免不了。除了誅仙陣,別無他法。」
「槐先生既然早有準備,就別藏著掖著了。」
這些年,槐堰早出晚歸,甚少在族中出現。
當時不明真相,只以為他看上了某個女子,偷偷幽會去了。
如今才明白,幾千年的時間,足夠槐堰將誅仙陣的陣腳悄無聲息地埋進人界。
他被我戳穿,倒沒太大的反應,解釋道:「聖女,都是為了妖族。」
「嗯。」
「宗吾的命,便不留了吧?」
我冷眼一掃,語氣帶了淡淡的警告:「槐先生,此事已有定論,不必再提。」
天邊烏雲滾滾,不多時,一場驚雷卷積暴雨,傾盆而下。
這個淒涼雨夜,我坐在宗吾身前,對著他,說了一夜話。
我說:「宗吾,我要死了。」
他說:「槐瑤,求你,撿起來。」
「你知道的,祭陣。其實死過一次,倒不怎麼怕了。」
「槐瑤,求求你,撿起來。
」
「你會跟我一起死,知道嗎?」
「別說了,撿起來,好不好?」宗吾的聲音幾乎哀求。
宗吾,我愛你。
在他猩紅的眼眶中,我仰起頭,在他乾澀的唇上落下一吻,轉身離去。
天明,一個大陣自天空中轟然落下。
頓時,萬裡風沙飛揚,哀鴻遍野。
槐堰籌謀千年,佈局精妙,大陣威力自然不弱。
「妖女,幾千年過去,沒想到你們還是如此,冥頑不靈。」
他們個個面色猙獰,恨不得將我除之而後快。
我懶得同他廢話,入陣劃破了手掌,熟悉的感覺再次襲來。
這一次,手指虛虛一握,那人便折斷了頸骨,破布一樣掉落山澗。
看到他們臉上的驚恐,我笑出聲來。
「多虧了你們聖僧,我才有今日。」
話落,他們臉上浮現出難堪與憤怒,「妖女,你莫要信口雌黃!」
我抱臂立在陣中,劇烈的罡風裹挾著利刃,撞向對方的屏障,「雙修的滋味,你們能享得,我不能嗎?」
「呸!不知廉恥!」
「交出聖僧,饒你不死!」
其實他們哪裡是為了宗吾來的。
妖族支脈繁多,除卻槐妖獨特的體質叫人垂涎,更有不少助他們精盡修為的妖族。
若宗吾不在,他們也會找個其他的理由,打上門來。
他們凝力化作一個巨大的長劍陣,指向我所在的位置,「那是陣眼!只要滅了她,妖族不攻自破。」
我冷笑著,只想速戰速決。
大陣發出一聲嗡鳴,罡風起,與劍氣摩擦,發出刺耳的鈍響。
眨眼間,敵方折損數千人。
四周的小妖在劍氣壓迫下,化作齏粉。
我咬緊了牙,額頭已佈滿冷汗。
「聖女。」槐堰望著我,突然將匕首插進自己小臂,走進來,「老夫也助你。」
「槐先生,我以為你捨不得死。」我聲音已經沒了開始的清澈。
槐堰沉著臉,「老夫說過,我們兩個,從來都是一道的。這一仗贏了,妖族從此光明正大地行走世間,而老夫為的,是我們槐妖一脈,在妖族中,揚眉吐氣。」
有了槐堰的助力,誅仙陣威力大增。
兩方相撞,地動山搖,雙方皆被震得後退一步,氣血翻湧。
我喉嚨口湧上一股腥甜,心脈突然狂跳不止,似乎有什麼要掙脫束縛。
我臉色一變,宗吾不見了。
然而對方沒給我思考的時間,上方的劍氣再度凝聚,對著我們當頭劈下。
此時雙方都處于強弩之末,稍有不慎,便死無葬身之地。
當!
又熬過了一下。
屍體已漫山遍野,有妖也有人。
天空猩紅,不見天日。
最後一次,劍氣與罡風狠狠撞在一起。
槐堰撲通一聲,倒下了。
我撲哧吐出一口鮮血,冷眼看著對方的人無聲地掉落,失去了平衡,對著地面栽下去。
大陣還未停止,由于失去了控制,開始瘋狂蠶食我和槐堰的血肉。倘若對方還有如我一般的苟延殘喘之輩,誅仙陣會做最後的收尾。
我跪在地上,眼前發黑。
喃喃道:「妖族弟子……聽令,日後務必振興妖族,不得為禍世間,不得傷人性命,以我一命,換來日榮景,望爾等珍之重之。
」
「謹遵聖女令!」妖族弟子呼啦跪倒一地,對著我拜下,哭聲哀切。
兩陣餘威仍在,妖族已悉數撤離。
扭曲破碎的空間自交界處,逐漸向我吞噬而來。
我張開手掌,最終無力地癱倒再地。
這次是真的要死了,宗吾……走了也好。
一點點金光將我漸漸圍攏,我聽到一聲歎息,努力抬起眼睛,是宗吾。
確切地說,是他的一個虛影。
他眼神悲憫,帶著哀切的沉痛。
「槐瑤,我要如何救你。」他輕歎一聲,虛幻的手似乎想摸過我的秀髮,最後卻徒勞地穿過了我的身子。
空間縫隙已近在眼前,宗吾滿眼不舍,似乎,有淚滑落。
我張開嘴,含糊地念到他的名字,卻見他笑著轉身,走入裂隙。
金光自黑暗中消失。
裂隙閉合。
風和雨漸漸停了。
一片廢墟裡,我踉蹌起身,怔怔望向宗吾消失的地方,煙霧散去,一個人站在那裡,渾身血跡。
我急急喊道,「宗吾!」
那人轉過頭來,眼神有過一瞬間的茫然,繼而對著我道:「貧僧初玄,見過施主。」
眼神是陌生的。
明明還是那具身體,被我咬破的嘴唇還未癒合,可他卻不記得我了。
身邊有人咳嗽一聲,緩緩坐起身,聲音嘶啞破敗,「那不是宗吾。」
我覺得槐堰被摔壞了腦子,皺著眉糾正他:「他是。」
槐堰苦笑道:「宗吾,已經走進去了。」
我短促地笑了一句,聲音尖銳,「槐堰,老眼昏花了吧,他進哪兒了?」
「你看見了。」槐堰指指裂隙消失的地方,「沒有他,我們已經死了。」
我的笑漸漸凝固,突然走到和尚面前,捧住他的臉,細細打量。
和尚眉眼淡淡,似乎並不抗拒我,但他還是緊緊皺起眉頭,「施主請自重。」
那一瞬間,我如遭雷擊。
過了很久,聲音晦澀道:「你不是宗吾。」
槐堰道,「如今他的身體裡,只剩一縷殘魂了。」
我幾乎發不出聲音,徒勞的,拽著和尚的衣角,眼眶通紅。
槐堰沉吟許久,緩緩道:「人妖殊途,變數良多,與其告知真相,亂你心智,毀妖族大業,我寧願瞞而不報。」
我沉默良久,啞著嗓子說:「槐先生,我和他,誰欠誰,總要算個明白的。」
槐堰道:「誅仙陣以殺止陣,你本是逃不過的。」
「……當年宗吾割裂神魂,將其中一部分化作佛印打入你的心脈,才讓老夫有妖丹可聚。」
我閉上眼,淚滑下來。
槐堰繼續道:「後來宗吾消失,我猜是他因割裂神魂而修為大損,不得已避世。」
「……後來,在你客棧周圍,我發現了一個和尚的蹤跡,便知他回來了。這些年,宗吾屢屢阻我佈陣,又找上你,我唯恐大業失敗,便暗中叫你毀他修為。」
我攥緊了手中皺巴巴的衣裳,「那夜,你可曾出手傷他?」
「不曾。」
在客棧見到他的那一晚,他受了傷,槐堰並未動手,所以,只可能是他做了什麼事,神魂再受重創。
我想到了那串佛珠,曾在戒律堂,為我擋過一次劫難,後來,又被我親手摔碎在宗吾面前。
宗吾的神魂,應該不止割裂過一次。
那夜進門前,他將第二次割下的神魂藏在了佛珠裡,趁著那晚,為我帶在腳上。
那東西,能救命。
所以後來,宗吾一次又一次求我將散落的珠子撿起。
可我將他牢牢定在牆上,極盡嘲諷。
直到大戰陷入焦灼。
在小屋裡,宗吾第三次割裂了自己的神魂,掙脫枷鎖,懷揣佛珠前來,替我擋下一劫,最終,消失在縫隙裡。
如今,只剩一縷殘魂擺在我的面前。
不識我。
不認我。
「槐先生,他為什麼,不說啊……」我站在原地,心裡好像破了個洞,空落落的。
「言之無用。」
便是他一五一十告知于我,我也只當他在狡辯,況且以宗吾沉默寡言的性子,不解釋才是他。
「還能找回來嗎?」我的聲音了無生氣。
槐堰歎了口氣,「去哪找?聖女,我知你並不想殺他,奈何他一心求死。放手吧,莫叫他連最後的神魂都同你牽扯上,不得安寧。」
我怔怔望向初玄,想到這是宗吾留在世上唯一的念想,突然撤了手,生怕驚擾他半分。
袖擺從指間溜走,我虛虛一握。
他兩手合十,對著我行禮,轉身,消失在視野裡。
我看著看著,突然哭出聲來,肝腸寸斷。
三年後。
我坐在枝頭,指尖變出一朵槐花,丟下去。
我是寶華寺門前的一棵槐樹,三年前紮根于此,平日裡化作真身往樹上一坐,便等著那個叫初玄的和尚從門內出來。
如今,他正坐在樹下,槐花落下他的肩頭。
誦經聲一頓,他無奈道:「施主怎麼又來了?」
我小聲道:「大師不用管我,我坐著吹吹風。」
于是,初玄繼續念他的佛經,我則坐在枝頭,繼續看他。
初玄的生活極其單調。
除了來此誦讀經書,便是寺院清修,去禪房打坐。
那些經文我早八百年就會了,他卻不厭其煩地念了又念,可謂鍾情。
山上的齋飯沒有油水,他瘦了一些,我輕歎一聲,落下枝頭,將兩個糖燒餅放在他身旁的石頭上,便要悄無聲息地走。
「施主,貧僧用過齋了。」
我腳步一頓,語氣晦澀,「這是我唯一……能給你的了。」
身後沒了動靜,我揉了揉眼,不敢待太久,躲到了樹後面。
我仍記得槐堰的話:「莫叫他最後一縷神魂,跟你牽扯上,不得安寧。」
不多時,有人自樹後繞過來,在我身前站定。
我紅著眼,抬頭,初玄穿了一身青色袈裟,神色清雋,對著我伸出手,「施主,地上寒涼,起來吧。」
我慌亂地向後退去,生怕碰到他的指尖,因為著急,蹲坐在地。
初玄一愣,繼而抱歉道:「貧僧唐突,驚擾了施主。」
我狼狽地從地上站起,後退一步,遠遠拉開了距離,「不會,我沒有這樣想。」
「貧僧覺得施主頗有佛緣,便將此物贈與施主吧。」
初玄攤開掌心,一串小小的佛珠躺在裡面。
我心開始鈍痛,不自覺流下眼淚。
伸出手,卻在半路握成拳,收回來。
「我……配不上這樣好的東西。」
初玄見我哭了,無奈笑道:「只是一串佛珠。」
我忙擺手,「不……你的東西都是好的……我……我先走了。」
說完,丟下初玄,落荒而逃。
槐堰沉默地坐在我對面,淡淡道:「初玄遲早會發現你的真身,到時候,你難道還要再胡攪蠻纏一次?」
我兩眼腫成核桃,槐堰早習以為常。
「三年了,世間再無宗吾的消息,該死心了。」
「槐先生,我有沒有說過,你的心腸很硬。」
槐堰不以為然,望向窗外,「妖族勢微,心腸不硬,如何走得下去。宗吾屢次救你,可重來一回,你未必想讓他救。你的心腸,也不軟。」
我低著頭,回顧過往,似乎最好的結局,是我與宗吾相忘于江湖。
他不必為我割裂神魂,而我,合該在當年,就殉在誅仙陣中。
槐堰站起身來,「我要走了。」
「走去哪兒?」
「隨便,也許,不再回來了。」
我茫然地點頭。
槐堰問我,「你呢?」
我沉默很久,「我再等等吧,民間有個說法,叫守喪。」
「三年,夠久了。」
「他等我三千年,我便為他守三千年。」
三千年,說長不長,說短不短。
昔日的初玄,再登頂峰,德高望重,信徒眾多。
現今的寶華寺,香火鼎盛。
而我,依舊是寶華寺門前的一株槐樹,只是後來不以真身出現了,生怕初玄發現我是妖邪,命人連根挖去。
初玄依舊每日在樹下打坐,剩下的時間,便盯著樹愣神。
開始佛門弟子總勸他,後來便不再勸了。
這一日,寶華寺來了個人。
雖然過了很久,我還是一眼認出了槐堰的身影。
他面容依舊,只是渾身枯槁之氣,仿佛大限將至。
初玄睜開了眼,靜靜看著他走來。
槐堰來到樹下,卻抬頭看我。
「他回來了。」
四個字,足以在我的內心掀起波瀾。
我不顧被人識破真身的危險,跌下樹來,「在哪兒?」
槐堰看向我的身後,「宗吾,恢復記憶很久了吧。」
我背影一僵,那一刻,突然不敢回過頭去。
在我還沒想好如何面對他時,身體突然落入一個溫暖的懷抱,「槐瑤,原來你在這裡。」
聲音清冷,卻溫暖。
槐堰淡淡看我一眼,那一眼中飽含譏誚,似乎嘲笑我心上人就在眼前,我卻傻等,連真身都不敢被人瞧見。
「槐瑤,老夫欠你們的,算是還清了。」槐堰丟在最後一句,背過身朝山下走去。
我從未有過如此複雜的情緒,喜悅,忐忑,愧疚,難過。
聞著淡淡檀香,我眼眶一紅,哽咽道:「你是宗吾嗎?」
「從很久以前就是了。」
他低下頭,在我臉上落下輕輕一吻,歎道:
「明明初玄的名字,被世人傳頌,寶華寺的美名,廣為流傳,可你卻沒來找我,直到剛才坐在樹下,我還在想,你到底在哪。」
「槐瑤,你知道等一個人,有多苦嗎?」
「一個三千年,又一個三千年。」
宗吾板過我的身子,拇指印在我濕潤的眼角,「明明糾纏那麼多次,為何這次放手了?」
他總能用簡潔的話語激發我心底的愧疚。
我哭得上氣不接下氣,「對不起,我不想害你……」
宗吾歎了一聲,「是我自願做的,倘若這些都換不來你的糾纏,才是真正的悲哀。」
原來,我每日坐在樹上等他的時候,他也在等我。
三千年,我把心反復揉碎,想了無數個可能,哪怕他常伴青燈,或是還俗再娶,我絕不糾纏。
我只要遠遠地,看著他就好了。
如今夙願得償,我突然說不出話來。
只好踮起腳,攬住宗吾的脖子,閉著眼吻上去。
我希望他能知道,我有多想他。
宗吾的手繞過我的腰肢,拉進自己,給予溫柔的回應。
我不知不覺軟了腿,伏在他懷裡,微微喘著氣。
宗吾一聲低笑,接著,門前傳來一聲怒喝:「妖女!膽敢勾引聖僧!」
我和宗吾同時望去。
唇瓣還腫著,宗吾的唇上留下一排小小的牙印兒。
佛門弟子滿面怒容,金缽在手,發誓要講我拿下。
我活了許多年,早已不怕這些小把戲,卻揪住了宗吾的袖擺,往他身後一躲,一如當年。
這一年的春天,槐花滿樹。
風吹過枝頭,吹落一地芬芳。
初玄聖僧還俗了。
他的袈裟,整整齊齊疊在樹下。
在世人不解的目光裡,他牽起我的手,對我說,「槐瑤,我來娶你。
」
封面:不負如來不負卿
作者:
來自「鹽故事」專欄《夫君修煉指南:寵妻的一百種方式》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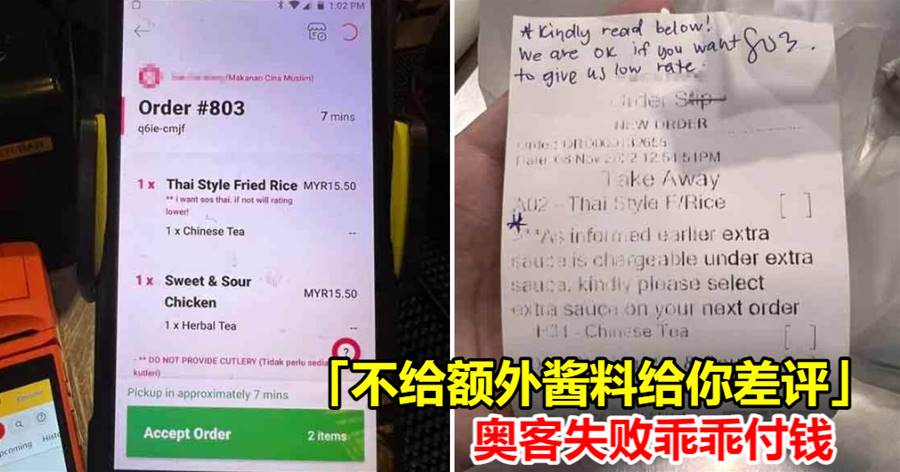

代表者: 土屋千冬
郵便番号:114-0001
住所:東京都北区東十条3丁目16番4号
資本金:2,000,000円
設立日:2023年03月07日
